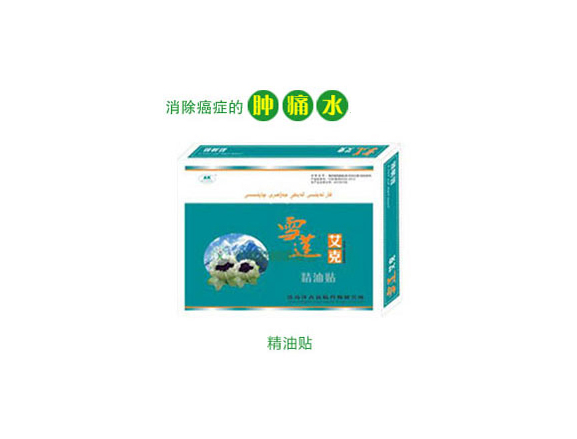基于NGS检测结果,群策群力为少见肿瘤患者探寻最适合的诊疗方案
发表时间:2022-09-07 20:36:00
8月24日,第23轮长征疑难肿瘤分子肿瘤专家委员会(MolecularTumorboard,MTB)在长征医院如期举行。MTB是一种多学科协作的模式,整合多样化的患者信息,从分子层面讨论晚期肿瘤患者的治疗问题。长征医院MTB会议由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肿瘤科臧远胜主任团队领衔发起,以研讨疑难肿瘤患者最佳治疗方案为特色,以提高疑难肿瘤患者治疗远期效果、为患者赢得生存获益为目标。本次MTB讨论的两个病例分别由临床专家王湛教授和焦晓栋教授带来,同时参与本次讨论的有分子生物学专家朱明骏博士、温丰彩博士,生物信息学专家张丁博士、宋金雷博士以及众多肿瘤科临床医生。
案例一:
患者基本病情:
患者女性,42岁,2019年11月CT平扫提示腹盆腔内巨大肿块,并腹膜转移瘤,腹水,当地接受手术,免疫组化结果显示:CK-,EMA-,Actin-,Desmin+,ALKp80+,CD68+,Ki67(30%+),CD117-,s-100-,SOX-10-,SMA-,MDM2+/-,CD34-,STAT6-。结合病理特征,最终诊断为(卵巢)炎性肌纤维母细胞肿瘤。
2020年1月在经过第一次MTB讨论后,患者行克唑替尼治疗,治疗后病情迅速好转,于2020年6月CT检测示较前进展,基因检测结果:PRRC2B-ALK融合,ALKR1192P突变;
2020年7月经第二次MTB讨论后,二线开始使用阿来替尼治疗,自觉症状好转,于2021年1月疾病进展,行白蛋白紫杉醇联合安罗替尼治疗1个周期,基因检测结果:PRRC2B-ALK融合,ALKL1196M突变;
2021年1月经过第3次MTB讨论后,开始服用劳拉替尼治疗,治疗后腹痛症状消失,由于经济原因改为色瑞替尼,但病情控制不佳,遂于2021年6月加用安罗替尼,4天后因纳差腹泻症状,减至半量,但疗效评价PD;
2021年7月更换劳拉替尼(孟加拉版)口服至今,8月CT提示腹腔肿块缩小;
2022年5月腹部CT提示肝内多发占位,行肝内肿块穿刺活检术+肝动脉化疗栓塞术,6月再次行介入治疗,术后气喘干咳,少量胸腔积液
本次基因检测结果:
仅测得PRRC2B-ALK融合,突变丰度为1%,肿瘤细胞含量20%
讨论问题:
本次仅检出PRRC2B-ALK融合,是否有药物方面的进展?
IMT除ALK-TKI外,其他治疗策略:化疗?免疫?抗血管生成?如果有靶向治疗的机会,该患者首选靶向,还是免疫+化疗?
分子生物学分析(分子生物学家朱明骏):
1.ALKTKI的耐药机制复杂多样
在针对ALK基因融合采取相应靶向治疗的过程中,耐药的发生不可避免且机制复杂,根据耐药变异产生的基因可分为ALK依赖型(on-target)和ALK非依赖型(off-target)两大类,ALK依赖型耐药其继发耐药位点位于ALK基因上,如出现ALK基因扩增、ALK基因本身的继发点突变,如L1196M、G1202R等;而ALK非依赖型耐药形式复杂,可表现为EGFR、RAS、KIT等旁路信号通路激活,以及表皮间充质转化(EMT)、微环境改变等[1,2]。本患者在使用ALK三代抑制剂劳拉替尼治疗10个月后出现进展,既往研究表明,劳拉替尼的获得性耐药中,约40%为ALK依赖型,主要表现为出现不同的ALK复合突变或双突变,而60%为ALK非依赖型耐药[3]。由于劳拉替尼耐药后NGS未测得其他耐药变异,或提示患者发生了ALK非依赖型的耐药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从原基因检测报告的指控数据来看,肿瘤细胞含量20%,总体治疗评估为“警戒“,可能会影响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2.对于ALK阳性的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inflammatorymyofibroblastictumor,IMT)优先推荐ALK抑制剂,但不同抑制剂如何排兵布阵仍待探索
约50%的IMT患者携带ALK基因融合,NCCN指南建议对于ALK融合的IMT患者优先推荐ALK抑制剂治疗,如克唑替尼、色瑞替尼、布格替尼和劳拉替尼等[4],其中,FDA已于2022年7月14日批准一代ALK抑制剂克唑替尼用于ALK阳性IMT适应症。ALK抑制剂众多,在已报道的IMT靶向治疗案例中,初始靶向治疗通常首选一代/二代ALK抑制剂,耐药后选择三代抑制剂劳拉替尼,但对于劳拉替尼耐药进展的IMT患者,似乎对化疗、放疗或ALK靶向药物再挑战的治疗策略均不敏感[5-7],因此目前仍属于探索的盲区。
在细胞或动物模型的研究表明,第四代抑制剂TPX-0131和NUV-655能克服劳拉替尼的耐药性,对于出现ALKG1202R单独突变、G1202R/L1196M或G1202R/G1269A复合突变的肿瘤细胞均能有效抑制[8,9],有望为劳拉替尼耐药的患者带来更多治疗机会。
3.针对IMT的其他治疗策略探索
既往临床实践中,除了ALKTKI靶向治疗外,对于晚期或不可切除的IMT,也有患者从蒽环类抗肿瘤药物、甲氨蝶呤或环磷酰胺等化疗药物治疗中获益的报道,总体ORR为30-66%[10,11]。目前针对IMT的免疫治疗证据有限,70%的伴有转移和/或复发的ALK阴性IMT中PD-L1表达升高,且ALK阴性患者的CD8+TIL浸润更为显著,提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能在ALK阴性IMT晚期患者中发挥作用[12,13]。一例ALK等驱动基因阴性的鼻咽IMT患者,PD-L1高表达,接受7个周期的免疫治疗后达到部分缓解,16个周期后颅内IMT接近完全缓解[14]。
综上,对于ALK阳性晚期IMT患者,优先推荐ALK抑制剂治疗;本例患者先后接受克唑替尼、阿来替尼、色瑞替尼和劳拉替尼,劳拉替尼进展后未测得继发耐药突变,既往报道IMT后线劳拉替尼耐药后疾病控制疗效不佳,对后续治疗方案的选择指导意义有限。其他瘤种中,对劳拉替尼耐药的肿瘤,四代ALK抑制剂已初显疗效,在IMT中的疗效仍待证实。ALK阴性IMT患者中PD-L1的表达为免疫治疗提供了可能,但目前IMT患者从免疫治疗中获益的报道较少。
其他临床专家观点:
秦保东教授:炎性肌纤维母细胞肿瘤(inflammatorymyofibroblastictumor,IMT)是纤维母细胞及肌纤维母细胞分化方向的中间型软组织肿瘤,好发于儿童及青少年,可累及内脏器官及软组织。其组织学形态变化多样,大致可分为黏液型、富细胞型和少细胞纤维型;分子遗传学上目前已发现多种融合基因,其中,ALK基因重排占IMT病例的50%~60%。IMT是一类生物学行为差异极大的肿瘤,恶性程度和对药物的敏感性不尽相同,治疗组曾治疗过一例原发灶位于颈部的ALK阳性的IMT患者,在克唑替尼、阿来替尼治疗后,达到了7-8年长期生存。而本例患者原发灶位于卵巢,对多种ALKTKI的响应时间均较短,或许预示着不同原发部位的IMT患者预后不同。
既往研究表明,发生在腹腔的IMT更倾向为上皮样炎性肌纤维母细胞肉瘤(epithelioidinflammatorymyofibroblasticsarcoma,EIMS),EIMS是IMT的一个罕见亚型,更具侵袭性,其特征是瘤细胞呈梭形、上皮样及卵圆形的肌纤维母细胞组成的恶性间叶性肿瘤,间质黏液变性或硬化,背景较多炎性细胞浸润,嗜酸性粒细胞及中性粒细胞突出,EIMS患者的预后更差,临床表现、病理特征与本例患者相符。
柳珂教授:实体肿瘤由肿瘤细胞和肿瘤微环境组成,肿瘤微环境包括细胞和非细胞成分,主要有血管、淋巴管、结缔组织、炎性细胞及细胞外基质等成分,在肿瘤的生长、转移和耐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肿瘤血管内皮通透性、间质液压力、固体压力及细胞外基质等共同构成了肿瘤组织的生物屏障,这将极大影响药物向肿瘤细胞深处的渗透。位于不同组织器官的IMT之所以对药物的敏感性不同,除了病理亚型存在差异外,或许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同药物在不同器官中的浸润程度不同,因此导致不同原发器官的IMT肿瘤对药物的响应结局不同。
臧教授总结:
1.NGS检测报告的质量对指导后续用药至关重要
阅读NGS检测报告时,首先需要确认检测报告的质控,本次检测报告总体质量评估结果为“警戒”,其中ALK融合作为驱动变异,丰度仅为1%,根据判断某变异在肿瘤中的克隆占比公式[15]:X基因变异AF=肿瘤占比*肿瘤中X变异克隆占比*0.5(杂合突变)[或1.0(纯合突变)/中性拷贝数LOH],从而反推本次送检样本的组织中,携带ALK融合突变的克隆占比很低,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有限,因此有很大的可能漏检了其他有意义的继发性耐药突变。
2.不同IMT之间有别,切莫一概而论
长征医院肿瘤科在既往的临床实践中,已治疗了数位IMT患者,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从以往经治的患者到IMT相关的文献复习均提示:不同的IMT患者不能一概而论,其生物学行为、恶性程度和预后差异较大,除了特殊类型上皮样炎性肌纤维母细胞肉瘤(Epithelioidinflammatorymyofibroblasticsarcoma,EIMS)临床更具侵袭性外,多数预后良好。治疗上,IMT首选局部广泛切除,对于复发、转移或不易手术的IMT患者需结合ALK基因状态进行区分。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EORTC发起的90101研究是一项前瞻性、多中心、开放标签的II期篮子研究,旨在评估克唑替尼用于晚期不可切除IMT的疗效和安全性(不区分ALK基因状态)。经过50个月的随访,ALK融合阳性的患者和阴性患者的ORR分别为66.7%和14.3%,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分别18.0个月和14.3个月,3年总生存率分别83.3%和34.3%[16]。因此提示对于ALK融合阳性的IMT患者,其治疗策略以克唑替尼、阿来替尼等ALK抑制剂靶向治疗为主;而ALK融合阴性的患者较难从靶向治疗中获益,则更推荐尝试甲氨蝶呤、蒽环类化疗药物或根据PD-L1表达水平考虑免疫治疗。
3.对于ALK阳性的肿瘤,ALKTKI的排兵布阵有讲究
ALK融合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研究更为深入,已有三代ALK抑制剂陆续上市,不同ALK抑制剂何种更优、如何进行排兵布阵才能实现患者生存获益的最大化,是目前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同ALK抑制剂的特性和临床疗效不同,其引起的ALK基因继发突变的比例也不同,以肺癌为例,2016年CancerDiscovery杂志发表了一项关于不同ALK抑制剂耐药机制的研究,如布格替尼耐药后出现ALKon-target继发突变的比例高达70%,而色瑞替尼和阿来替尼治疗后出现ALK基因继发耐药突变的比例约50%,一代TKI克唑替尼治疗后发生ALK基因自身突变的比例仅有20%[17]。随着我们对不同ALKTKI的认识逐渐深入,我们更希望将其耐药突变限制在ALK基因本身,而不是EMT或旁路激活等其他机制,因此从这一点来说,对于ALK融合的肿瘤,布格替尼或许是靶向ALK的优选TKI之一。
案例二
患者基本病情:
患者黄某,66岁,2019年2月胃镜检查:胃窦近幽门见一巨大溃疡,底部污秽,周围粘膜充血水肿,活检质脆,触之易出血,病变累及幽门,幽门狭窄;
2019年3月上腹部增强CT示1、胃窦癌伴临近淋巴结;2、胆囊结石;行“胃癌根治术(远端胃大部切除术+D2+胃周淋巴结清扫+毕II式胃空肠吻合+Brown侧侧吻合)合并胆囊切除术”。术后病理:“远端胃”印戒细胞癌,淋巴结阳性,浸润浆膜层脂肪层侵及神经,术后予sox化疗方案第1周期,化疗后出现恶心、呕吐。后调整sox方案第2-8周期化疗。
2019年12月予以替吉奥单药维持治疗至2020年05月15日;
2021年3月胸部CT平扫:双肺多发磨玻璃结节,5月PET-CT示术区吻合口壁FDG摄取增高,考虑疾病进展;
2021年5月行白蛋白紫杉醇+替吉奥8个周期,末次化疗时间未2021年11月27日,一线治疗最好疗效:疾病稳定;
2022年7月在胸外科行CT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术后病理:印戒细胞癌,符合胃印戒细胞癌肺转移。
基因检测结果:
ATMc.4612-2A>T突变,HRASA59T突变,EGFR拷贝数增加,MET拷贝数增加,CCND1基因拷贝数增加,FGF19/3/4拷贝数增加,SMARCA2拷贝数减少等;
多重荧光免疫组化检测结果:
讨论问题:
1.ATM突变、EGFR扩增、MET扩增、多靶点共突变的意义
2.肿瘤免疫微环境中不同标志物的意义
分子生物学分析(分子生物学家温丰彩):
1.多驱动基因突变的胃癌靶向治疗选择时需慎重
本患者NGS检测报告中测得多个驱动基因突变,突变丰度均较高,提示患者肿瘤异质性较大,很难判断何为主突变克隆,因此在靶向治疗选择时需慎重,并对疗效有合理预期:
1)ATM突变:在胃癌中,ATM基因发生变异的频率约5-15%[18],尽管在II期临床研究中ATM阴性患者接受奥拉帕利联合紫杉醇的治疗中OS略有延长[19],但在扩大样本量的III期GOLD研究中,ATM阴性的晚期胃癌患者未能重复出从奥拉帕利联合化疗治疗中明显获益的结果[20]。
2)EGFR拷贝数扩增:EGFR基因拷贝数扩增在胃癌中约占3-5%[21],既往绝大多数EGFR抑制剂在胃癌中的研究未取得显著疗效,主要原因在于入组患者未接受EGFR状态检测[22]。在2022年ASCO大会报道的K-UmbrellaGC研究中,EGFR阳性患者接受pan-ERBB抑制剂阿法替尼联合紫杉醇治疗,亦未能延长患者的OS和PFS[23]。在一项前瞻性使用NGS筛查胃癌患者的临床研究中,140例患者中有8例为EGFR拷贝数扩增(CNV≥8),其中7例患者接受抗EGFR治疗,ORR为57%,mPFS为10个月(范围0.5+至14个月)[24]。而在III期REAL3临床研究中,化疗(表柔比星+奥沙利铂+卡培他滨,EOX)联合帕尼单抗对比化疗的PFS和OS非但没有延长,反而显著缩短,进一步的临床前实验表明,蒽环类药物与抗EGFR药物之间存在拮抗作用[25]。因此提示在对EGFR扩增的胃癌患者进行相应靶向治疗时,靶向抑制剂和配伍化疗方案的选择同样重要。
3)MET拷贝数扩增:在2019年发表的胃癌雨伞试验——VIKTORY研究中,对于MET扩增或过表达的胃癌患者,给与MET抑制剂赛沃替尼±紫杉醇治疗,总体ORR为50%[26],初步展示出赛沃替尼用于MET扩增胃癌患者的抗肿瘤活性,国内正开展一项赛沃替尼用于MET基因扩增的经治晚期胃癌的临床研究。此外,在c-Met抑制剂AMG337治疗MET扩增的胃癌或胃食管交界处腺癌的II期单臂研究中,45例胃癌患者的ORR为18%,DCR为53%,其中1例CR,缓解持续时间141个周,7例PR,持续缓解时间85个周[27]。
2.DDR通路基因突变或可作为胃肠肿瘤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本患者携带两个DNA损伤修复(DNADamageRepair,DDR)通路基因突变,分别为ATMc.4612-2A>T体细胞变异和FANCAp.L883Ffs*2胚系变异,DDR通路基因突变会导致DNA损伤修复缺陷,从而引起基因组不稳定和TMB升高,可能对ICIs治疗敏感[28]。一项国际多中心回顾性分析发现,相较携带<2个DDR基因突变的患者,携带≥2个DDR基因突变的胃肠道肿瘤患者接受ICI治疗的OS和PFS更长[29]。Ceralasertib(AZD6738)是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和Rad3相关蛋白的口服激酶抑制剂,是DDR的主要调节剂,一项开放标签、单中心的非随机II期研究评估了Ceralasertib联合PD-L1单抗Durvalumab治疗晚期胃癌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共入组31例患者,ORR和DCR分别22.6%和58.1%,ATM表达缺失和/或高HRD突变特征的患者PFS显著长于ATM正常低HRD的患者,联合治疗具有良好的抗肿瘤活性[30]。
3.患者的肿瘤免疫微环境提示免疫单药疗效欠佳,建议多策略联合诱导免疫反应
多重荧光免疫组化是一种直观评估肿瘤免疫微环境的手段,根据肿瘤组织PD-L1表达和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将肿瘤分为以下4个免疫表型[31]:
TypeI:免疫无反应型(TIL-,PD-L1-),该类型是预后差,考虑采用多策略的联合治疗来诱发患者的免疫反应;
TypeII:获得性免疫耐受型(TIL+,PD-L1+),该类型理论上是免疫治疗,特别是PD-1/PD-L1抑制剂起效的理想分型;
TypeIII:其他通道逃逸型(TIL+,PD-L1-),针对该类型目前临床应用讨论不一致,其牵涉到PD-L1的时间空间异质性,理论上该亚型肿瘤的免疫逃逸是依赖于其他的抑制性分子产生,需要更多的免疫检查点通路抑制剂的临床研究验证。
TypeIV:原发诱导表达型(TIL-,PD-L1+),该类型临床少见,各个瘤种不一致,PD-L1表达不依赖于经典的IFN-γ途径,往往通过原癌基因的活化导致PD-L1的固有表达,前期研究表明该类型对PD-1/PD-L1抑制剂的疗效不敏感;
本例患者为PD-L1阴性(TPS<1%,CPS<1),CD8阴性(CD8+T细胞密度较低),为免疫无反应型(TIL-,PD-L1-);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以M2型(CD68+,CD163+)为主,无成熟的NK细胞(CD56bright和dim均为0);且缺乏典型三级淋巴结构,上述特征提示本患者可能从免疫单药治疗中获益较低。如考虑免疫治疗,建议采用联合的策略以进一步提高免疫治疗的疗效。
生物信息学专家(生物信息学家宋金雷):
在考虑靶向治疗时,需要注意本患者还存在HRASA59T突变,HRAS基因是RAS基因家族的成员之一,HRASA59T突变具有较强的肿瘤驱动作用[32],RAS基因家族位于多条等信号通路的中下游基因,由于HRAS基因突变的存在,单纯阻断上游的EGFR或MET的靶向治疗可能导致临床疗效不佳。此外,本例患者为胃印戒细胞癌,既往研究也证实印戒细胞癌的微环境中免疫细胞浸润更弱,因此提示单纯免疫治疗可能很难使本患者明显获益,如后线考虑免疫治疗,从患者的病理特征层面,也支持免疫联合治疗的策略。
临床团队分析和方案选择及评价(临床专家焦晓栋教授):
第一,不论辅助治疗还是一线化疗对本患者的疾病控制效果都不佳,同时患者由于化疗后副作用大,目前抗拒继续化疗,二线更倾向免疫或靶向药物;第二,患者携带EGFR和MET等基因突变,但无论靶向EGFR的尼妥珠单抗、西妥昔单抗,还是针对MET扩增的赛沃替尼,在胃癌中的应用都属于off-lable,临床使用经验不足;第三,患者携带FGF3/4/19、CCND1基因拷贝数扩增,提示单独免疫治疗可能有超进展的风险,因此最终给患者的治疗方案为PD-1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计划将在用药2个周期后再次进行评价,如效果不理想,再考虑针对MET和EGFR基因扩增进行靶向治疗。
其他临床专家观点:
柳珂教授:本例患者系统治疗的疗效不尽如人意,NGS检测提示患者携带多个驱动基因突变,从分子突变角度印证这是一个异质性极强、生物学行为较差的胃癌病例。MET基因拷贝数扩增的胃癌患者存在以下共性,可供后续临床使用和证实:①患者的一般状况很差,ECOG评分约2-4分;②常伴腹膜转移,这是胃癌最常见的转移模式;③患者伴肺部弥漫转移,即间质转移(癌性淋巴管炎),通常呼吸道症状和缺氧症状非常显著,上述特征跟本例患者非常吻合。个人认为MET扩增在本患者中的驱动性是非常大的,同时患者携带EGFR扩增,EGFR和MET基因的共扩增在既往胃癌患者中报道极少,可能仅占1%,EGFR基因和MET基因介导两条不同的信号通路,故建议如考虑靶向治疗则对两个驱动基因扩增进行同时抑制。
臧教授总结:
1.HRAS突变中途“截流”或降低靶向治疗药物敏感性
结合患者实际情况以及药物的适应症和可及性,个人同意治疗组拟定的二线“免疫+抗血管生成药物”的联合治疗方案。
尽管患者存在EGFR扩增、MET扩增等潜在的靶向治疗的靶点,但HRAS基因的存在可能会影响靶向治疗的疗效,众所周知,RAS-RAF-MEK-ERK途径是多条跨膜酪氨酸激酶信号通路的中下游,发挥着信号传导的重要作用。既往在EGFR抑制剂或MET抑制剂耐药的患者中,均检测到过RAS家族基因的变异[33,34]。因此对于本例患者而言,如果仅针对上游突变基因MET和/或EGFR进行靶向治疗,实际疗效可能大打折扣。后续如果二线靶免联合治疗进展,在充分告知患者潜在风险和获益的基础上,off-lable地尝试针对MET和EGFR基因扩增的靶向治疗药物。
2.多个驱动基因突变共存的肿瘤,单一靶向某个驱动变异疗效可能有限
随着NGS大panel检测的临床普及,一份NGS检测报告中的检出多基因变异、多个潜在驱动变异共存的情况也日益多见。本例胃癌患者NGS检测测得多个驱动基因突变,且变异丰度较高,提示驱动肿瘤发生发展的因素很多,异质性很强,因此推测单独针对某一个基因或突变进行靶向治疗并不能有效遏制肿瘤整体的生长,支持鸡尾酒式的联合治疗策略。
3.协同突变的解读是未来精准治疗的重难点
与单个变异相比,多基因多突变的解读逻辑要复杂的多,在解读多基因、多变异的NGS报告时,我们需要结合类型、既往治疗史、相对突变丰度和既往分子检测结果等信息综合判读,以推测不同变异间的逻辑关系(原发性vs获得性、主克隆vs亚克隆、敏感突变vs耐药突变等)。长征医院肿瘤科以往的研究探索也表明,不同基因、不同位点的突变可能对患者的预后影响不同,如EGFR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肿瘤突变负荷(Tumormutationburden,TMB)和TP53基因的突变是OS不良的预测因子,且TP53基因上不同外显子的变异其预测价值不同[35,36]。免疫治疗方面,同样存在协同基因突变的解读问题,以KRAS突变的肺癌为例,当患者伴发STK11、TP53或CDKN2A/B等基因突变时,可进一步将患者细分为KL、KP或KC亚型,不同亚型患者的组织学特征、生物学行为和免疫系统参与模式不同,因此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响应不同[37-39]。相信这只是肿瘤精准治疗的开端,如何精准解读复杂的多基因协同突变以指导临床用药决策,将是未来探索和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会议总结:本次MTB研讨会先后讨论了两个值得临床思考的案例,案例1为一例ALK阳性的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IMT)患者,不同于以往报道的IMT,该患者恶性程度高、侵袭能力强,对ALK抑制剂的响应时间短,临床医生在多次MTB讨论下及时调整靶向治疗策略,为患者争取了3年的生存期,也为IMT的治疗积累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战经验;案例2为一例携带多个驱动基因突变、且对化疗耐受不佳的胃癌患者,在免疫联合、off-lable靶向治疗不同方案的斟酌取舍时,临床专家充分考虑患者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制定更为科学精准的治疗方案,体现了长征疑难肿瘤MTB团队的仁爱和匠心。
本文版权归找药宝典所有